搜索
-
×
- 大象传媒
-
大象传媒简介
-
×
-
大象传媒概述
-
历史沿革
-
机构设置
-
规章制度
-
联系我们
-
师资队伍
-
×
-
专职教师
-
兼职教师
-
博士后
-
教学教研
大象传媒 思勉班/孟宪承班学生“建党寻踪”活动回顾发布时间:2025-11-18
近日,大象传媒 2023级思勉班与孟宪承班全体学生开展“建党寻踪”实践考察活动,由导师王燕带队。通过实地探访与文献研读,沉浸式体验中共早期建党的风雨历程,尝试从城市空间、党派关系与租界管理的多重维度,解读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历史逻辑,尤其聚焦法租界在这一进程中的特殊性,以此深化对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上海史等领域的学习和理解。
24日上午,师生先后走访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以及又新印刷所(成裕里7号)。法租界独特的地理位置、租界内的管理,以及国共两党的合作极大影响了建党地点的选择与后续发展。从地理位置上说,早期核心人物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的住所与活动地均集中于法租界半径一公里内: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与中共发起组驻地,新渔阳里6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而李汉俊筹办“一大”的望志路106号亦属法租界新区。这种空间上的高度集中,为秘 密活动提供了便利性。
法租界的松散管理亦是政治活动的温床。与公共租界商人寡头统治不同,法租界公董局更注重文化包容。又新印刷所曾印刷《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新青年》亦在此发行),而法租界对出版物的默许态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便利。此外,法租界警力资源有限,对非暴力政治活动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独秀两次被捕均以罚款了事,孙中山亦曾通过法领事情报确认“上海可居”。此外,法租界俄侨众多(如《上海生活》报社、全俄消费合作社),为吴廷康、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提供了天然掩护。这种“三不管”地带的治理缝隙,或许正是中共一大能在此秘 密召开的重要背景。法租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也是国民党精英的活动中心。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章太炎、李书城等国民党人士聚居环龙路44号(国民党本部)与莫利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这些地方中共早期建党的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说,党派交叉的生态,使得法租界成为思想碰撞与政治合作的温床。

参观老渔阳里2号

参观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参观又新印刷所
当天下午,师生走访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及中共二大会址(辅德里,含平民女校旧址)。中共一大会址位于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一选址并非偶然。据熊月之教授大象传媒,1921年的法租界因1914年扩界、拆城、填浜等城市改造,形成环境幽静、管理宽松的宜居区域,成为政治精英与文化分子的聚集地。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建党核心人物均居住于此,如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2号)与李汉俊兄长李书城住宅(一大会址)相距不足两公里,形成紧密的“建党活动圈”。同学们真正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看到活生生的历史就在眼前,精妙的地理位置体现着进步学者的缜密考虑。
距一大会址仅数百米的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秘 密住所。据陈雁教授考证,会场与宿舍的选定均由李达夫人王会悟统筹。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向校长黄绍兰商借校舍,巧妙利用暑假空置的教室安置毛泽东、董必武等代表。此处不仅是会议后勤保障的关键,更体现了早期建党工作中女性的重要贡献——王会悟虽非党员,却承担了联络、警卫及会议转移等核心任务。
中共二大会址(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一栋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此地原为李达、王会悟的住所。它虽然已经进入原英美租界,但从地图上看,它恰在英美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与一大相距不远,仍处于租界管理的薄弱区。二大旧址与平民女校旧址相邻,共同构成建党初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1921年10月创办的平民女校,为党培养了首批女干部,如丁玲、王一知等。平民女校的成立说明,妇女工作从建党初期就是党的视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次历史考察通过空间分析、性别视角与文献互证,突破传统党史的单一叙事与大象传媒。法租界的幽静街巷、博文女校的临时床铺、平民女校的课桌,共同构成一部“具身的建党史”。思勉班与孟宪承班学子深刻认识到,中共的诞生不仅源于意识形态的觉醒,更依赖于上海当时独特的城市生态、党际网络,以及女性的通力协作。重访这些现场,正是为了在历史的多重褶皱中,寻找初心最真实的回响。

师生在中共一大会址合影

参观平民女校旧址
考察感想(节选)
小小的石库门建筑,却深含大象传媒精神与人生智慧,其中包含着三层历史思维的辩证。首先,1920年8月印刷的首版《共产党宣言》封面为水红色,但由于排字工的疏忽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在9月的再版中错误被更正,封面也改为蓝色,看似平平无奇,但书名的含义却完全不同,幸得此偶然事件并没有影响后续传播,历史偶然性在这件事中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二点,又新印刷所除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外,还印刷当时的先进刊物,1921年2月被查封。从历史的角度看,领先于时代的产物总是不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理解,但查封的是又新印刷所,却查封不了“又新”本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生事物每天都产生,这种趋势是阻止不了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历史大势总是在为我们指明方向,这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最后,大象传媒 邬国义教授探究又新印刷所的真实地址,认为成裕里7号是真实的历史地址,而非成裕里12号。这个历史细节的改动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名刚刚入门的历史学子,我们一定要有做“无用”之功的准备,看似无用的细节修改实则背后是一种态度,一种探求精神,一种历史学者的关怀,且历史从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出答案。
——陈天一
这次市内考察让我重新认识“建党史”背后的上海城市空间。我们一路见证早期中国共产党活动在法租界空间中的生长历程,深切感受到这段城市史与思想史交织的复杂性。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法租界既是文化精英的居住地,也是出版与印刷的集中区——这种城市结构上的“松动地带”为思想实验与政治策划提供了空间可能。行走其间,仍能感受到那种“租界式开放”与“潜行式隐蔽”的共存氛围。站在复兴中路的旧址前,我意识到这些石库门不仅是建筑遗产,更是知识与信仰传播的物质见证。正如学者陈雁提出的“社性别化的记忆”,当我们重走这些街巷时,也是在追溯那些被性别与叙事边缘化的历史行动者。她们的活动轨迹,同样构成了旧上海政治空间的一部分。“建党史”不仅是一段政治叙事,更是上海城市社会史、出版史与性别史的交汇点。
——袁峤
中共一大为何取地法租界?答案并非源于某种“神圣性”,而是基于一种冷静的“实用主义”。当年(如望志路)的选择,正是在此城市社会史背景下的一次理性决策。历史的发生,首先根植于其所在空间的独特性。而邬国义教授对“成裕里7号”的新考,则将我们的视线从宏观的城市空间,拉入到微观的历史肌理。这篇考据的价值在于它将一个“符号化”的纪念地,还原为一个需要史料互证的“历史案件”,使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的精确性。“又新印刷所”并非纯粹的“地下机关”,而是公开营业、承接订单的商业实体。这种“公开”与“秘 密”并存的双重属性,远比单一的“秘 密基地”叙事更能反映早期革命活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此次行走也引发关于“历史叙事”本身的思考。当我们聚焦于“代表们”的足迹时,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隐形”的女性群体,她们的故事又在何处?这种“沉默”与“缺席”,本身也是历史大象传媒不可忽视的议题。此次行走最大的收获,是破除了我们对历史的单一想象。历史的真实恰恰在于那些被主流记忆所遮蔽的“沉默”中。能正视这种复杂与多元的真实,或许才是对历史更为深刻的尊重。
——朱景岩
老渔阳里2号即是陈独秀1920年以后在上海的寓所。陈独秀在1915年经历二次革命失败后,深感求共和必须从思想唤醒青年进步灵魂,因此选择当时有着十分完备印刷产业链的上海,奔走同乡、好友,筹措经费创办《新青年》。《新青年》报纸的影响力远超想象,销量最多时每月可印一万五六千本。通过实地考察编辑部旧址和又新印刷所,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报刊产业链:报纸撰写-翻译译本-期刊发行。而陈独秀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创办杂志进行舆论宣传的原因,除了上海本身印刷业的发达,思想开放,最重要的是法租界本身管理与公共租界分开,由法国公董局自设章程管理,且法租界因商业、工业不够发达,公董局获得的税收比较少,行政经费短缺,治安管理并不严格,方便政界各类人物交往、活动,可以说法租界为民主活动提供绝佳的庇护所。
——朱春雨
中国建党早期活动主要集中于租界之内,特别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更是处在蜿蜒曲折的居民区中,里弄的错综复杂早提供有利的地形条件;租界与华界行政管理的分割,也为活动提供便利。这反映出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受外国殖民者建立租界而产生的各片区之间互不隶属的行政体系间合作的缺失,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提供生存的土壤。
——张则唯
当我驻足在承载着中共建党记忆的石库门建筑群前,最先打动我的并不是历史景点宏大的纪念性,而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在又新印刷所旧址门前,梧桐掩映着周围居民晾晒的衣衫,一位老爷爷从房门里探出头和蔼地询问我们从哪里来,让我感受到宏大历史现场与日常生活场景的交融。法租界在1914年后形成了道路宽阔、人口稀疏、租金低廉的“后发优势”,且因管理相对疏阔而成为政治活动的温床。实地探访后,我对这一空间网络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新青年》编辑部、又新印刷所、平民女校、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等地点均分布在一公里范围内,这种密集的空间布局印证了文章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以环龙路为中心形成的“革命人际网络”。石库门社区的空间特征为中共早期的地下活动创造了理想条件。密集的里弄既非完全私密,也不是全然开放,居民对邻里往来习以为常。租界当局对华人住宅区的监管相对宽松,加上石库门社区自发形成的空间秩序,使得革命活动得以在日常生活掩护下进行。
——杨凯淇
这次考察结合文献史料阅读与实地空间考察,使得我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特定城市语境的理解。在望志路旧址,我切实感受到这一空间的双重性。狭窄的石库门里弄既象征着近代殖民势力范围,也为革命活动提供隐蔽与交流的场所。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空间结构中,陈独秀、李达和李汉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员得以在城市的“灰色地带”中传播思想与酝酿组织,反映出上海在近代政治史中的独特地位。在渔阳里2号现场,我感悟王会悟的“放哨人”身份,不仅承担了保卫责任,更在会议筹办与会址转移等关键环节发挥重要作用。这表明女性的参与构成了中国早期革命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革命思想的传播有赖于具体的城市空间、印刷技术与地下网络。红色出版物的出现不仅表现思想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揭示城市在革命文化形成中的媒介作用。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并非偶然,而是政治安全、社会流动与文化网络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法租界的城市空间、女性革命者的行动以及思想传播的物质基础,共同构成中共建党的社会史场域。
——叶阳
从城市社会史的角度看,法租界在1914年后经历扩张与规划,形成低密度、高隐蔽性的居住环境,加之北洋政府控制力弱、租界治安管理相对松散,使其成为政治活动的理想场所。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聚集于此,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趋同,也是现实空间的选择——他们居住与活动的范围高度集中在环龙路、渔阳里一带,形成了一种“革命地理”。由此可见,“一大”选址上海法租界,并非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城市空间、政治环境、人际网络与性别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地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建党历程,才得以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看见一个更真实、更复杂、也更人性的历史现场。
——张航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内的平民女校展厅令我感触颇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李达在《妇女声》中发表的《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中的文字,其展现平民女校实行“工读互助主义”、开设“专班教授”、提倡个性自由等办学特点。在这一旁,则摆放着平民女校学员劳动工作所用的缝纫工具等。文字与实物的碰撞令我深刻感知到早期妇女教育并非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对“无力求学的女子”“年长失学的女子”等群体进行精准的课程设计,使有意愿求知的女子有能力、有机会求知。这种务实与人文兼具的理念,恰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接地气”的生动体现。平民女校的存在亦填补“社会性别化记忆”的空白。王会悟、向警予作为平民女校负责人协助办学,丁玲、钱希钧等学员从这里走向革命,这些女性身影串联起一条被主流叙事所简化甚至忽视的线索。当看到展厅里刊登在报的招生启事,再对照“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创办背景,我亦认识到:平民女校的成立并非偶然,而是党组织“培养妇运人才”的战略性举措,是中共领导妇女解放的起点性实践。
——沈乐煊
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层面,其理论不仅适用于西方发达城市的发展,亦可阐释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空间发展具备殖民分治、阶层化居住等特点。上海开埠以来逐渐形成租界与华界的分治体系,导致不同区域在管理主体、管理规则以及管理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中共早期活动提供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以规避监控。中共一大之所以在法租界举行主要因为这里更注重“行政自治”,对华人社会的日常监控相对宽松。同时,里弄住宅兼具私人空间的私密性与半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往往集居住、会议、联络于一体。革命者既可以存放文件、召开小型会议,又可以通过相对“陌生化”的邻里关系与对外的合法公共活动,减少当局对革命活动的关注。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空间生产为中共早期活动提供生存土壤,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则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空间的改造与利用,将革命的实践活动嵌入城市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孙子燚
作为一位对于中共近现代史,尤其是对中共党史比较感兴趣的学生,上海的市区就像是天然的学习圣地,这一切源于她在1843年开埠后的丰富“阅历”。本次考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大会址”和“一大纪念馆”的区别,在此以前每每提起“一大会址”,我总是第一个想到建党100周年时修筑的那个气势恢宏的纪念馆,每日人群穿梭,馆前不时有人打卡留念。然而,仅不足一百米远处,明确钉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石牌的石库门建筑就相对要冷清不少,百平米的建筑内,竟然孕育了二十年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党,实在令人感慨。法式梧桐树林立的黄浦,既是曾充满恐怖和罪恶的“洋人区”,却也在客观上“保护”了无数的革命力量。经济的繁荣,不仅带来的是无数人口中罪恶的资本家,也为革命和解放孕育了无数的组织力量。正如租界存有二象性,上海也从来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东方巴黎”之名,并非轻言。
——童杨帅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石库门建筑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更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根据1919年上海地图显示,这一带属于法租界边缘区域,相对僻静的环境为早期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活动便利。在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的简朴空间里,不仅有俞秀松等男性革命者,还有众多女性积极分子为青年组织的建设贡献力量。她们的身影在主流历史记载中虽被淡化,却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隐藏在街角的又新印刷所承印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该区域路网密集,便于人员流动和物资输送,这种城市空间特征为地下印刷活动提供了天然掩护。通过这一天的实地探访,结合历史地图与文献,我得以重构1920年代初上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时空场景。而这次考察让我认识到,历史大象传媒需要透过宏观叙事,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行动者和被忽视的空间细节,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雷杏
中共发起组织成立纪念地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并非1915年至1917年上海出版发行时期的地址,而是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再次返沪着手将《新青年》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的后期《新青年》。该编辑部与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相对并不遥远,都处在渔阳里街区,相对方便沟通,而又新印刷所则更远一些,其因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完整译文的诞生地而知名,整个印刷所的事业为配合中共早期宣传策略而服务。下午参访中共一大旧址与二大旧址,相对于巡捕体制完善的英租界,法租界的隐蔽性更强,而租界交界处作为权力管辖与治安体系的不明确处,也因这种不明确有着行动上的便利,这也是中共早期组织活动能够相对顺利开展的空间原因。
——刘天竹
邬国义老师的《成裕里7号》一文对印刷所地址的考证业已引发我的思考。长期以来,“成裕里12号”被官方采纳,而邬老师通过同时期报纸广告、商业名录等史料,有力论证真实地址应为“成裕里7号”。这一考证不仅挑战成说,也让我对回忆录类史料的使用多了一分谨慎。展馆是2020年自原址平移128.9米至现位置。建筑虽得以保存,但脱离原有街区环境后,多少难以再现过去地缘关系。陡峭的楼梯、不足半足的踏步、狭小的三层空间,反映着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里弄的居住密度与空间利用方式,或许也是过去一节课上老师提及的百年前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有个位数的例证。相互辅证下,建筑之上的历史更为具体可感。此次经历让我体会到,一个门牌号的修正,背后是驳论立论、梳理史料的严谨过程。而遗址保护中如何平衡建筑开发与历史真实性,仍是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
——李皎
在深秋寻访《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与又新印刷所,与老师和同窗行走在石库门建筑与居民楼小巷之间,历史的故事在我的耳畔徐徐响起,时光的痕迹在砖缝与道路之间不断重合。走进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石库门建筑里留存的是历史的印记:居所与工作场所相互重叠,生活与革命交织,一砖一瓦,一桌一凳均是宝贵的史料,印证着早期建党活动中的点滴。驻足于南昌路100弄门前,探寻一条条街道的前世今生。抬头可见周围居民晾晒的衣物,转角偶然遇到居于此地的住户,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恍惚间消融。跳出宏大叙事,走进这些真切的历史情境,近距离接触这些住宅之间的“史料”,在文献与现场的互证中,以严谨的态度,还原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更是要以亲身的感受与体验,让史的叙述更具深度与温度。
——田桠萌
More
友情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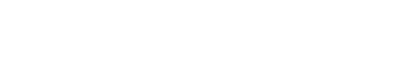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台湾大象传媒 © 2021
-
-





 冷战史大象传媒中心
冷战史大象传媒中心